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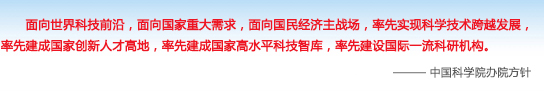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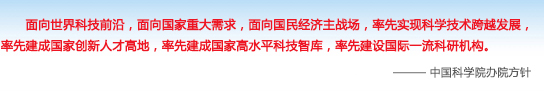
沒有誰還能期盼誰做什麼。
Photo Credit: Stockport Hydro Limited 競標制度之外還有其他選項嗎? 由以上的風險分析得知,小型參與者參與招標一旦未得標就需負擔龐大的成本流失風險,但是對於資本雄厚的大型能源集團而言,他們可以提供較低利潤的計畫,以損失來講,兩者之間並不對等。其中主要爭議在於,競標法案中增設特殊條款之作法能否如預期地增加投資者的多樣性?由於特殊條款對於競標結果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大型再生能源企業為順應不同的門檻必須發展出不同的策略,而其中,與居民能源組織等小型參與者合作成為一個變通方法 [5]。

簡單而言,競標制度的設計很可能造成能源參與的多元特性遭受動搖。此外,這些小型投標者可在得標後延長計劃實行的時間至兩年,來完成所得標的再生能源設施。而小型參與者也可透過合作,降低競標為他們帶來的風險。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95%得標者均為小規模再生能源組織,共佔1000MW,且這些得標團體均適用於「特殊條款」[3]。他建議,BImSchG許可證應該要成為參與競標的先決條件,而非在得標後才取得。
德國實施再生能源競標法規後,於2017年5月19日舉行第一輪風機競標。其餘不需經由競標的再生能源類型,尚包括生物燃料、水力發電、地熱、污水氣、礦氣、垃圾掩埋沼氣等。以氣候溫良、豐饒膏腴絕不遜於這東亞桑梓的美洲大陸,甚至未能發育出完整的穀物種植型的農業文明,就由於對資源的掠奪型開發而突然神祕地發生了文明崩潰。
有人算過一筆帳:黃河、淮河和海河三個流域的土地面積占全國的十五%,耕地、人口和GDP分別占全國的三分之一,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七%。近海赤潮頻發,渤海魚資源告罄,已是「空海」。後加入的兩國,偏又跟幾件東西密不可分:高人口密度,廉價勞力,還有一個喜馬拉雅山。也許,東亞比南美延長了一千年的文明壽數,在漫長的地質年代或環境年代裡,原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環境的報復才剛剛開始,唯其是災難的初始,又充滿了神祕的感應。
《國家地理》雜誌提供了一個範例。首都北京的水資源緊缺程度已經超乎想像,目前主要靠過度開採地下水勉強維持,迫切地等待南水北調二○一四年中線通水到北京。

北方河流都出現斷流,一九九七年黃河幹流斷流二百二十六天,整個河口斷流里程接近八百公里。三千五百萬年前啟動的印度板塊構造性撞擊(tectonic crash)歐亞板塊,隆起了喜瑪拉雅山,中尼邊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和世界屋脊西藏高原。華夏文明由黃河、長江孕育,是所謂「河流文明」,她卻從二十世紀末,開始發生嚴重的「水危機」。拉丁美洲土著(indigenous)在北部墨西哥沙漠地區,是無定居(漂流)方式,利於狩獵和採集,小族群並且社會結構簡單。
這個新的海拔高度,轉換了氣候型態,在北部形成沙漠,卻以印度洋之雨季浸淫其南部。從宏觀框架來看,大自然的恩賜實在是塞翁失馬。叢林居住的土著以狩獵為主,但茂盛的雨林環境也可發展農業,使其處於半定居狀態。在珠三角、長三角,一百公里的河道上,工廠密集,多到上千家,而中國竟然只採用歐美國家極輕微的「汙染排放標準」,而且企業不必花錢治理汙染,只需交納輕微罰單。
文:蘇曉康 東亞桑梓與生存空間 「全球化」這個時髦概念,既不是純經濟學的,也無文明內涵,有點半生不熟,讀了種種說法,還是五里霧中,後來乾脆拆解得簡單一點來看,才恍然大悟,原來在歐美發達國家(G8)之外,再加上一個中國,一個印度,便是「全球化」了,跟這個星球的其餘地方不搭界。五大湖湖容劇減,水質汙染。

這麼一塊膏腴之地,其幾千年的經濟開發模式,近來有人反省,稱為「吃祖宗飯,奪子孫路」的方式。第五種因素「貿易和貿易轉讓」,因該大陸的與世隔絕而不明顯。
這個撞擊在四川盆地的東緣龍門山斷層,撕開了口子,而那裡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深山密林的綿陽安縣,就有五十萬人,因而殺傷之慘重,乃是無從避免的。那麼,在四千年的中國文明史裡,無論「崩潰五點框架論」套不套得上,這個最長壽的農業文明卻至今沒有崩潰,要麼就是它對環境、自然的破壞掠奪並不劇烈,要麼就是這套模式只是從美洲文明中設計出來的,擺到東亞就失靈了。長江十年之內將變成「第二條黃河」。地質運動間隙中的人類文明,該有怎樣的「環境意識」呢? 另外一個未解之謎,卻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百零九位,是一個貧水大國。太湖流域、海河流域,是兩個汙染最嚴重的流域。
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黃土高原,在《禹貢》土壤分類的等級中被載為「上上一等」,曾經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經過上千年掠奪式的開發,成為一片荒山禿嶺,水土流失嚴重,大量泥沙被沖進黃河,形成了世界罕見的「懸河」。半定居土著建村落,但遷移頻繁,以休耕輪種,巴西歷史上著名的土著社會「Tupi」,就以宗族和耕種作業分類組成社會,而不是以階級,他們也沒有帝國。
熱帶土壤稀薄,茂密的植被給人錯覺,似乎肥力無限,事實上熱帶雨林驚人的生命力只存在於昆蟲、林木,以及沒有根莖在土壤裡的樹林寄生菌類中國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百零九位,是一個貧水大國。
後加入的兩國,偏又跟幾件東西密不可分:高人口密度,廉價勞力,還有一個喜馬拉雅山。近海赤潮頻發,渤海魚資源告罄,已是「空海」。
五大湖湖容劇減,水質汙染。這個新的海拔高度,轉換了氣候型態,在北部形成沙漠,卻以印度洋之雨季浸淫其南部。首都北京的水資源緊缺程度已經超乎想像,目前主要靠過度開採地下水勉強維持,迫切地等待南水北調二○一四年中線通水到北京。長江十年之內將變成「第二條黃河」。
這個撞擊在四川盆地的東緣龍門山斷層,撕開了口子,而那裡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深山密林的綿陽安縣,就有五十萬人,因而殺傷之慘重,乃是無從避免的。叢林居住的土著以狩獵為主,但茂盛的雨林環境也可發展農業,使其處於半定居狀態。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發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八級,地震界的解釋是來自印度板塊的撞擊,千萬年尚未底定的一個地質運動。從高原冰河流出來的中國生命線長江黃河,徜徉東去,雖漸次低落,卻依舊跌宕,江河流域孕育的沃壤,風調雨順滋育的大地,使中國文明出現於西元前六千五百年之際,世界上第一個種植穀物、馴養家禽的地方,其供養的人口終於成為世界之最。
半定居土著建村落,但遷移頻繁,以休耕輪種,巴西歷史上著名的土著社會「Tupi」,就以宗族和耕種作業分類組成社會,而不是以階級,他們也沒有帝國。熱帶土壤稀薄,茂密的植被給人錯覺,似乎肥力無限,事實上熱帶雨林驚人的生命力只存在於昆蟲、林木,以及沒有根莖在土壤裡的樹林寄生菌類。
太湖流域、海河流域,是兩個汙染最嚴重的流域。文:蘇曉康 東亞桑梓與生存空間 「全球化」這個時髦概念,既不是純經濟學的,也無文明內涵,有點半生不熟,讀了種種說法,還是五里霧中,後來乾脆拆解得簡單一點來看,才恍然大悟,原來在歐美發達國家(G8)之外,再加上一個中國,一個印度,便是「全球化」了,跟這個星球的其餘地方不搭界。拉丁美洲土著(indigenous)在北部墨西哥沙漠地區,是無定居(漂流)方式,利於狩獵和採集,小族群並且社會結構簡單。華夏文明由黃河、長江孕育,是所謂「河流文明」,她卻從二十世紀末,開始發生嚴重的「水危機」。
第五種因素「貿易和貿易轉讓」,因該大陸的與世隔絕而不明顯。以氣候溫良、豐饒膏腴絕不遜於這東亞桑梓的美洲大陸,甚至未能發育出完整的穀物種植型的農業文明,就由於對資源的掠奪型開發而突然神祕地發生了文明崩潰。
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黃土高原,在《禹貢》土壤分類的等級中被載為「上上一等」,曾經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經過上千年掠奪式的開發,成為一片荒山禿嶺,水土流失嚴重,大量泥沙被沖進黃河,形成了世界罕見的「懸河」。此外,中國六百個城市中有四百個缺水,一百一十個嚴重缺水。
也許,東亞比南美延長了一千年的文明壽數,在漫長的地質年代或環境年代裡,原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環境的報復才剛剛開始,唯其是災難的初始,又充滿了神祕的感應。三千五百萬年前啟動的印度板塊構造性撞擊(tectonic crash)歐亞板塊,隆起了喜瑪拉雅山,中尼邊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和世界屋脊西藏高原。




© 1996 - 2019 平流缓进网 版权所有联系我们
地址:新化街